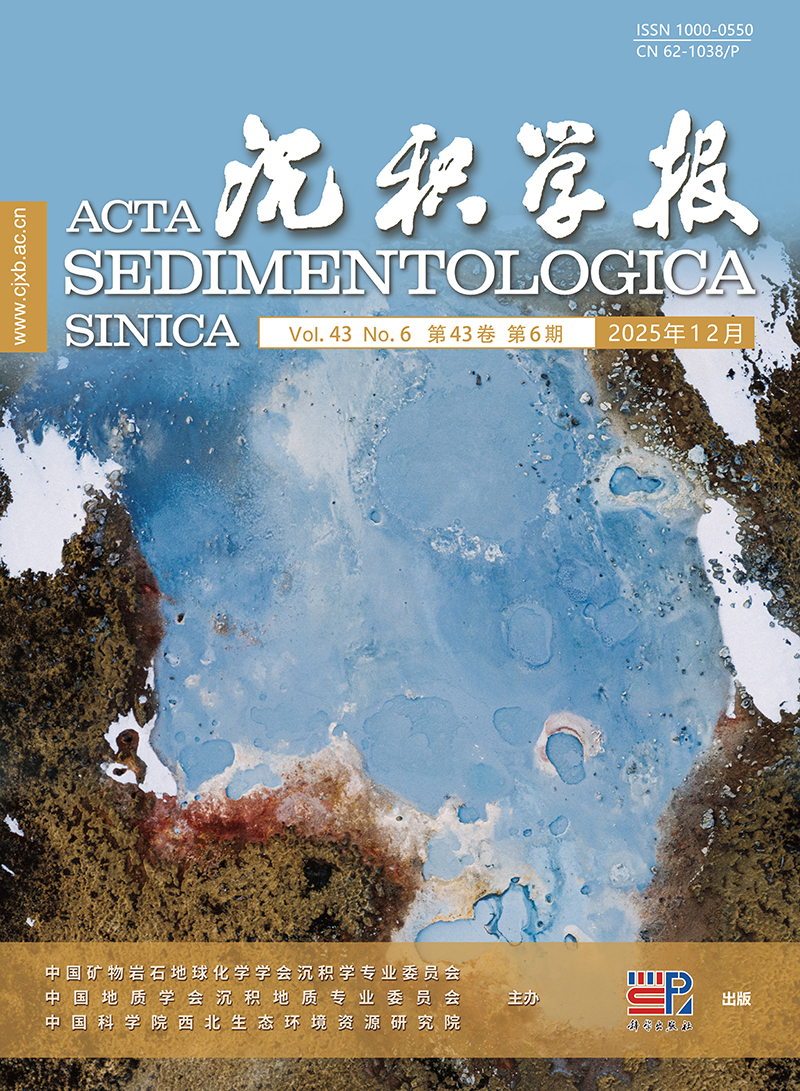提要:本研究聚焦于PETM前短时碳脉冲事件(POE)在东特提斯塔里木海的完整记录及其全球意义,通过多指标高分辨率沉积序列,结合地球系统模型cGENIE的双重反演模拟,确认POE是一个全球同步、百到千年尺度的“闪电式”碳释放事件,并量化了触发POE的碳源性质与释放特征。研究揭示了短时碳脉冲对全球快速增温的响应机制及其作为PETM前奏事件在碳循环失稳过程中的作用。
1.研究背景
距今约5600万年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PETM)是中生代以来最剧烈的全球变暖事件,源于约2千到1万3千Pg(1 Pg = 10亿吨)碳在短时间内(千年至万年时间尺度)快速注入海洋-大气系统 (Cui et al., 2011; Gutjahr et al., 2017) (沉积之声:高分辨率天文年代学视角下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这次巨量碳释放导致大气CO2浓度急剧升高,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约5–6 °C,海洋酸化加剧和缺氧扩散,引发了广泛的生态响应 (McInerney and Wing, 2011),诸如热带生物扩张至中纬度地区,深海底栖有孔虫约半数物种灭绝,陆地哺乳动物出现显著的“侏儒化”等。
PETM的标志性地质证据包括全球分布的碳同位素显著负偏(CIE,2–6 ‰),以及碳酸盐补偿深度(CCD)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超2 km,导致大量碳酸钙沉积消失并形成红色黏土层 (Zachos et al., 2005)——反映了海洋快速酸化和全球碳循环强烈扰动。因其极端温室效应和生态冲击,PETM被视为研究全球变暖与碳循环耦合机制的经典地质案例,为理解当前和未来的人为气候变化提供深远启示(Foster et al., 2018)。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质与地球物理证据表明PETM碳释放与北大西洋火成岩省(NAIP)岩浆侵入有关(沉积之声: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致因的直接证据)。挪威近海地震剖面显示,岩浆侵入富含有机质地层,诱发接触变质和热解反应,释放大量甲烷和CO2等温室气体,通过海底喷口进入海洋-大气系统,触发了PETM (Svensen et al., 2004, 2012; Berndt et al., 2023)。该火山-沉积盆地驱动、多种反馈“放大”的机制已获数值模型支持 (Gutjahr et al., 2017; Kender et al., 2021)。
值得注意的是,PETM发生之前,地质记录中还存在一个时间更短、幅度更小的碳同位素负偏事件(图1),被称为“PETM前幕碳漂移事件”(Pre-Onset Excursion, POE) (Bowen et al., 2015)。这一“前兆”事件最早在美国怀俄明州Bighorn盆地古土壤中被发现,随后陆续发现于北美大西洋沿海平原、西南太平洋以及欧洲西部的北海盆地和比利牛斯前陆盆地等浅海相沉积记录中。POE事件的典型特征包括:(1)碳同位素负偏幅度约1–2 ‰;(2)持续时间短,仅数百年至数千年;(3)伴随中等增温、浅层海洋酸化和富营养化;(4)生态扰动较PETM温和。由于POE持续时间极短,在深海沉积物中易被生物扰动和碳酸盐溶解“抹去”, 通常仅在高分辨率的陆相和浅海记录中才能被识别,在过去长时间内未引起足够关注。尽管规模较小,POE期间仍出现了小幅气候变暖和碳循环扰动。随着浅海和陆相高分辨率记录的积累,以及地球系统模型的应用,研究者逐渐认识到,POE或许正是PETM这场气候灾难的前奏——一次地质时间尺度上“闪电式”的碳释放扰动了原本接近平衡的碳库,拉开了PETM序幕。
图1. 古新世和始新世早期古气候变化(改自Svensen等, 2012)。海洋温度变化根据微体化石氧同位素估算。58–50 Ma全球逐渐变暖,期间多次出现短暂的极热事件,POE发生于古新世末,紧接着就是最为显著的PETM。52–50 Ma全球进入早始新世气候最适宜期(EECO),达到最暖峰值,随后开始逐渐降温。
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对比研究深时气候事件可以帮助认识当代全球变暖的特殊性。尽管PETM和POE等事件的碳释放速率已属地质史上“很快”,但相比之下,现代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碳排放速率仍远超其上(Cui et al., 2011; Kump, 2011; Cui et al., 2021)。模拟表明,PETM碳释放峰值速率约为0.3–1.7 PgC/年(驱动~5°C变暖),而当今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速率(~10 PgC/年)是PETM的6–30倍。由于当今大气中的CO2增长在速率和规模上都前所未有 (Zeebe et al., 2016),而即便像PETM这样剧烈的碳释放事件,其速率仍不及当代人为排放,这意味着现今气候系统正面临比远古更严峻的冲击。通过深入研究PETM及POE等事件,可以更好地理解快速碳脉冲对气候和生态的影响,从而为评估未来风险提供借鉴。更值得警惕的是,PETM的全球气候效应——增温~5°C、深海缺氧、生态扰动——都是在这样一个远低于当前排放速率的背景下发生的。POE研究进一步提醒我们:即便是百-千年尺度的“短暂碳脉冲”,其速率若达到某一临界值,同样可以触发显著的气候响应乃至系统失衡。
因此,系统认识POE的持续时间、碳源机制、排放强度及其在全球的地层记录,不仅有助于厘清PETM的“起爆机制”,更能为评估当代碳排放的潜在风险提供深时参照。
2. 塔里木盆地高分辨率POE-PETM地质记录
本研究选取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部库孜贡苏剖面为研究对象。古近纪早期,该剖面位于东特提斯海地区,当时属于海平面上升形成的一种陆表海环境,古水深约30–50 m (Jiang et al., 2023),属于受限的浅水碳酸盐台地环境(图2)。该海区在古新世-始新世之交是温暖、高盐海水的汇聚区和有机碳埋藏的重要场所,对当时海洋碳循环具有关键影响。库孜贡苏剖面地层连续,产出丰富的钙质超微、牡蛎化石,有机质含量高,为高精度年代地层和多指标古环境分析提供了良好条件。
图2. 库孜贡苏剖面位置与古地理。(a) 56 Ma古地理分布;(b) 研究区早古近纪古海水等深图;(c) 库孜贡苏剖面现今位置;(d) 剖面露头照片。
库孜贡苏剖面位于喀什乌恰县,实测约48米厚,以平均10 cm间隔开展高分辨率采样,覆盖了POE和PETM事件层 (Wang et al., 2022)。综合运用多种地球化学指标,包括碳同位素(碳酸盐岩和有机质的δ13C)表征碳循环扰动,汞(Hg)含量与Hg/TOC指示火山活动,有机质C/N比值判别其来源,CaCO3%评估海洋酸化和陆源稀释,微量元素作为海洋营养和化学风化指标,以及生物标志物示踪海洋微生物群落等。此外,基于磁化率的功率谱分析显示剖面中存在21 kyr岁差周期和100 kyr偏心率周期沉积旋回,通过旋回分析建立了高分辨率年代框架 (Chu et al., 2025)。
为揭示POE的碳源性质以及碳释放速率与总量,使用了中等复杂程度的地球系统模型cGENIE进行模拟实验。创新采用“双重反演”方法,将实测的表层海洋δ13C和pH变化量作为模型约束条件,调整模型中的碳注入情景,使模拟结果再现POE期间观察到的碳同位素负偏幅度和海洋酸化程度。通过多组敏感性实验(不同POE CIE时长、不同pH变化量ΔpH),估算了引发POE事件所需的碳释放总量、速率以及碳源同位素组成。
3.核心发现与科学意义
3.1 百-千年尺度的POE具有全球性影响
基于多指标分析结果,POE-PETM期间东特提斯洋经历了极端增温、浅海酸化、富营养化和初级生产力增强,伴随陆源输入增加和微生物群落重组,浅海环境呈现出低氧化趋势(图3)。这些特征与全球同期记录一致。此外,POE和PETM对应了Hg/TOC峰值,可能与北大西洋火成岩省(NAIP)活动相关,为碳循环扰动和温度升高提供火山活动线索。
图3. 库孜贡苏剖面POE和PETM记录特征。TEX86和牡蛎团簇同位素温度显示在PETM恢复阶段塔里木海表层温度仍高达30℃。
高分辨率记录清晰地显示,在PETM之下约8.4米处存在一个约1.2米厚的钙质页岩,记录了1–2.5 ‰的δ13C负偏,此即为POE(图3、4)。POE在该剖面的持续时间短至仅约4000年左右(其他地点POE大致在数百年至几千年不等)。沉积与生物指标显示,虽然POE造成的环境扰动相对于PETM要小得多,但在事件过程中表层海洋依然出现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图4),包括碳循环迅速失衡、海水酸化和缺氧程度的增加 (Dong et al., 2024),以及初级生产力和浮游生物群落的波动。这些证据表明,即使是百年到千年尺度的一次短暂碳排放脉冲,也足以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可识别的气候和环境响应。这一发现凸显了地球系统对快速碳输入的敏感性:短时间的大规模碳注入会打破碳循环稳态,引发连锁的气候效应和生态扰动。
图4. 基于代用指标重建的东特提斯库孜贡苏剖面POE-PETM环境变化。
3.2 POE峰值碳排放速率达现代水平,推高大气CO₂浓度350 ppm
基于pH-δ13C耦合约束,cGENIE模型反演结果显示:为解释POE事件约1–2.5 ‰的δ13C负偏和推测的海洋酸化程度,大气CO2分压(pCO2)需从事件前约830 ppm猛增至1200 ppm以上,较背景值升高了约370 ppm(图5)。换言之,在短短的千年时间尺度内,大气CO2浓度上升了约45%。
图5. cGENIE模拟的不同年龄模型下的大气pCO2(a-d)和海表温度(SST,e-f)变化。POE期间大气pCO2峰值高达1180–1220 ppm,增加约350–390 ppm(背景值830 ppm),SST升高约1–2 °C。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POE的碳释放速率。cGENIE模拟结果显示,POE期间的峰值碳释放速率约为1 PgC/年(范围0.2–1.3 PgC/年;图6),与工业革命初期人类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强度相当。需要指出的是,地质历史上典型的碳释放事件(包括PETM)平均速率通常不到1 PgC/年 (Cui et al., 2011, 2021; Kump, 2011),而POE的碳释放速率接近于1960s人类活动的碳排放强度,远低于当前全球超过10 PgC/年的排放水平。
尽管如此,在自然条件下如此高的碳注入速率依然导致了约1–2 °C全球表层海洋升温(模型模拟ΔT为1.1–1.3 °C;图5),这一结果与基于北大西洋浮游有孔虫Mg/Ca比值的古温度重建所观测到的百至千年尺度内~2°C升温幅度一致 (Babila et al., 2022)。这表明,即便是在短时间尺度内的快速小规模碳排放,也足以引发显著的气候变暖和海洋环境变化。
PO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天然实验”:与如今人类引发的“闪电式”碳排放相比,POE在排放速率上低了一个量级,却依然造成了全球变暖和碳循环扰动。这提示我们,当前持续加快的碳排放极有可能带来更剧烈的气候和环境影响,并潜藏触发系统临界反馈和不可逆变化的风险。正如IPCC报告所强调的,当前大气CO2增长速率在地质历史上前所未有,人类正将气候推向未知领域。
POE的发现印证了“小幅但快速”的碳脉冲同样能够产生全球效应,提醒我们当前的人类排放速率已进入一个极为危险的区间,需要引起高度关注。POE期间碳释放总量估计在1000–1800 PgC之间(图6),上限恰好达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碳排放的累计总量,为理解 PETM 前奏事件的碳排放特征和全球气候效应提供了重要的定量参考。
图6. 不同POE持续时间情景下cGENIE模拟的pH-δ13C双重反演结果:(a-d)碳源的δ¹³C值;(e-h)碳释放速率;(i-l)累计碳释放量。灰色阴影表示1500年时间窗口。
3.3 火山热成因碳释放触发POE并引发气候反馈
通过整合高分辨率地质记录与cGENIE模拟,推断POE的碳来源主要来自北大西洋火成岩省(NAIP)岩床侵入有机质地层时产生的热成因CO2。在PETM发生前,大西洋裂谷地区正处于NAIP岩浆活动的初始阶段,岩浆以岩床形式迅速侵入富含有机碳的沉积盆地,导致接触“烘烤”作用,大量13C亏损的CO2和甲烷被释放 (Gutjahr et al., 2017)。这些温室气体通过热液通道喷射进入海洋-大气系统,触发了POE地质档案中记录的δ13C负偏和全球升温。cGENIE模型计算结果进一步支持这一机制:只有假设碳源以火山热解CO2(δ13C约−20‰)为主时,才能使模拟结果中的ΔpH和δ13C变化幅度与实测POE数据相匹配。相反,如果假设碳源以生物成因甲烷(δ13C接近−60‰)为主,则在相同碳注入量下会导致过度的海洋酸化和δ13C负偏,显著偏离观测值。因此,最符合证据的情景是:岩浆侵入引发大量CO2在POE期间以“闪电式”速率释放,导致全球气候的快速响应。值得注意的是,地球动力学模型表明,NAIP 岩浆活动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达0.5 PgC/年的碳排放通量 (Jones et al., 2019),这一数值与POE所需的峰值排放速率高度一致,显示NAIP完全具备触发类似POE这种碳脉冲事件的能力。
然而,POE 事件可能并非完全由火山碳单独驱动。在初始增温和酸化背景下,地球系统中的其他碳库(如海底甲烷水合物和陆地有机碳库)可能被激发,形成正反馈机制。研究推测,POE期间热成因CO2排放引发的增温与海洋环境变化进一步削弱了碳库的稳定性,可能促发了生物成因甲烷的额外释放。这一机制类似于“引爆火药”,即一次规模相对较小的热启动使气候系统跨越了临界阈值,从而引发了紧随其后的大规模碳释放和极端变暖(即PETM)。
对比POE和PETM,两者在性质上既有联系又有差异:POE的δ13C负偏幅度仅约1–2.5 ‰,远小于PETM高达3–6 ‰的剧变;POE的持续时间和涉及碳量也明显较小。然而,正是这一相对微弱但快速的“前奏”扰动,可能触发了地球系统的临界转变,迅速引发了PETM灾难性碳释放和极端变暖。换言之,POE在机制上扮演了PETM的“导火索”角色,其发生表明当时气候系统已被推至不稳定的边缘,一旦受到扰动便迅速跃变。NAIP岩浆活动早期阶段即可引发诸如POE的全球气候响应,为后续更大规模释放引发灾难性气候环境剧变创造了条件,这一发现填补了POE与PETM之间因果联系的关键空白。
4.对现代气候变化启示
POE和PETM等深时碳释放事件为我们理解当今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启示。POE是PETM前的一次百至千年尺度的小规模快速碳排放事件,其排放速率仅为当前人类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速率的十分之一,却已在短时间内引发显著的全球变暖、海洋酸化和生态扰动。这一事件清晰表明,气候系统对快速碳注入高度敏感,即使排放规模和速率远低于当今水平,也可能引发气候和碳循环的非线性响应,激发如甲烷水合物和永久冻土碳释放等反馈,形成“加速变暖-反馈释放-进一步变暖”的恶性循环。
这提醒我们,不能以线性思维去推断人类持续排放的后果,历史上的气候“惊涛骇浪”常在跨越临界点后突然爆发。当前全球变暖已出现北极冻土融化、部分海域甲烷升高等预警信号,显示气候系统可能正在逼近“临界阈值”。如果我们继续沿着高排放情景前进,人类社会可能面临超越PETM的剧变场景,其影响将远超现代社会的承受范围。
深时研究还提示气候恢复的极端缓慢与长期性。若碳排放总量可控,类似POE规模的碳排放可在千年尺度内通过深海混合作用相对快速恢复,然而,这一时间尺度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依然沉重且难以承受;若排放持续累积至PETM规模,地球系统将耗尽深海碳库的缓冲能力,恢复过程将依赖生物泵和硅酸盐风化等极慢机制,需以万年计,几乎等同于永久改变地球环境。PETM期间曾发生大规模物种迁徙和部分海洋生物灭绝,但生态系统最终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逐步恢复。然而,我们不能仅因 POE和PETM未造成全球性生物大灭绝而自我安慰:人类文明历史短暂,且现代生态系统在栖息地破碎化和多重压力下更加脆弱,使我们比古代生物更易受到气候剧变的冲击。
综上所述,对百-千年尺度“闪电式”碳脉冲事件POE的深入解读,增强了我们对气候系统阈值、快速反馈机制及长期影响的理解,凸显了尽快减排行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深时地质记录清楚表明,如果在碳排放积累到引爆点前及时止步,人类可避免加速变暖和生态失控的最坏结果;反之,一旦跨越临界阈值,再补救为时晚矣。正如Lee Kump等学者所言,人类仍拥有缩减排放、降低风险的机会窗口,但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POE和PETM事件为当今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唯有汲取地球历史的经验教训,立即采取有力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才能避免“重演PETM”事件。毕竟,5600万年前大自然已经为我们上演过一次“快速碳排放实验”,人类理应谦逊地从中汲取教训,而不是亲身去尝试一次。
本文第一作者是海南大学、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姜仕军教授,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Ying Cui副教授和姜仕军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合作者海包括海南大学王亚苏副研究员,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Maurizia De Palma博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David Naafs教授,南京大学胡修棉教授、蒋璟鑫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吴怀春教授、褚润健博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谷阳光研究员,北京大学王久源助理教授,布里斯托大学黄一舟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Miquela Ingalls助理教授、Timothy Bralower教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杨石岭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James Zachos教授,以及加州大学河滨分校Andy Ridgwell教授。相关成果于2025年6月30日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
详情请阅读原始文献:Jiang, S.*, Cui*, Y., Wang, Y., De Palma, M., Naafs, B.D.A., Jiang, J., Hu, X., Wu, H., Chu, R., Gu, Y., Wang, J., Huang, Y., Ingalls, M., Bralower, T.J., Yang, S., Zachos, J.C., Ridgwell, A., Millennial-timescale thermogenic CO2 release preced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5, DOI: 10.1038/s41467-025-60939-3
参考文献
Babila, T.L. et al., 2022. Surface ocean warming and acidification driven by rapid carbon release precedes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Science Advances 8, eabg1025.
Berndt, C. et al., 2023. Shallow-water hydrothermal venting linked to the Pala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Nature Geoscience 16, 803-809.
Bowen, G.J. et al., 2015. Two massive, rapid releases of carbon during the onset of the Pala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Nature Geoscience 8, 44-47.
Chu, R., et al., 2025. Eccentricity pacing of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Multi-section astrochronology and statistical insights in China.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49, 104800.
Cui, Y. et al., 2011. Slow release of fossil carbon during the Pala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Nature Geoscience 4, 481-485.
Cui, Y. et al., 2021. Massive and rapid predominantly volcanic CO2 emission during the 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 e2014701118.
Dong, Y., et al., 2024. Paleoenvironment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stern Tethys during the pre-onset excursion preceding the PETM.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647, 112234.
Foster, G.L. et al., 2018. Placing our current ‘hyperthermal’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climate change in our geological past.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376, 20170086.
Gutjahr, M. et al., 2017. Very large release of mostly volcanic carbon during the Pala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Nature 548, 573-577.
Jiang, J. et al., 2023. Eustatic change across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in the epicontinental Tarim seaway.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29, 104241.
Jones, S.M., et al., 2019. Large Igneous Province thermogenic greenhouse gas flux could have initiated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climate change.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
Kender, S. et al., 2021. Paleocene/Eocene carbon feedbacks triggered by volcanic activity. Nature Communications 12, 5186.
Kump, L.R., 2011. THE Last Great Global Warming. Scientific American 305, 56-61.
McInerney, F.A., Wing, S.L., 2011.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A Perturbation of Carbon Cycle, Climate, and Biosphere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39, 489-516.
Nunes, F., Norris, R.D., 2006. Abrupt reversal in ocean overturning during the Palaeocene/Eocene warm period. Nature 439, 60-63.
Svensen, H., 2012. Bubbles from the deep. Nature 483, 413-415.
Svensen, H. et al., 2004. Release of methane from a volcanic basin as a mechanism for initial Eocene global warming. Nature 429, 542-545.
Wang, Y., et al., 2022. Response of calcareous nannoplankton to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in the Paratethys Seaway (Tarim Basin, West China).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17, 103918.
Zachos, J.C. et al., 2005. Rapid acidification of the ocean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Science 308, 1611-1615.
Zeebe, R.E. et al., 2016. Anthropogenic carbon release rate unprecedented during the past 66 million years. Nature Geoscience 9, 325-329.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5-60939-3
图文 | 姜仕军 崔莹